□ 李泽乾
一日,我暂离南京的别寓,回到滁城的家中,从落尘的旧物和泛黄的信堆里寻觅往日的感慨,偶尔窥见了父辈的青春和缱绻。
那是数摞陈旧的信笺,静置在书架一隅,深藏在书卷深处,约莫有近百封。在浮尘的洗礼、时间的浸染之下,原先杏黄鲜亮的信封已沉淀出近乎古铜的棕褐色。信封上斑驳点缀、交替呈现的,正是父亲和母亲的名字,以及他们尚在求学时的住址所在。这些便是父母尚未结为连理,尚在青春年华徜徉时的往来书信。
我信手捡来几封父亲写给母亲的信,小心地展开,三十余年光阴的啃噬下,盈握在手中的信纸已经薄如蝉翼。父亲的笔触周密而从容,尺牍相接、优游舒畅的字迹之下,蕴藏着饱含爱慕和思念的心情。自我记事以来,便生长在规整近乎严苛的家教之下,父亲对他和母亲相识相恋的奔放年华讳莫如深,因此我也只好以信取人,从行文中揣测他不同的手迹所映射的丰富内心。
有时,父亲写信有如工匠刻画,笔触工整,字迹清雅,字里行间极尽从容不迫。除了简约描述日常之外,多叙触景生情、感物伤怀,抑或是畅叙思念,娓娓道来,动人清听。有时,父亲写信犹如笔挟风雨,满纸烟云,寥寥数页,驰骋着忧思和关切,更兼彼时他与母亲相隔两地,劳燕分飞,多有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的离愁别绪。再有时则介于二者之间,行文不温不火,笔触周密而诙谐,文风爽朗而大方,多诉欣慰憧憬之意。
我草草翻阅数篇,其中最引我瞩目的,是父亲写给母亲一封信中的《戒烟辞》。日夜相思辗转,更兼学业劳苦、校务芜杂,父亲求学时便开始与烟草相伴。每受母亲嗔怪与关切,父亲决意“挥惠剑,斩烟丝”,便在给母亲的信中写下戒烟誓词。他回顾自己吞云吐雾之时“敷衍心面,固属可怜”,但又痛恨自己“虚与委蛇,欲壑难填”,历数吸烟“日计不足,月计万千”的亏空,最终决意“及早觉悟,回头是岸”。在信中,父亲称自己将《戒烟辞》悬于床头,复又将其抄录信上,寄与母亲共勉。至今日,我也几乎未见父亲在家中吞云吐雾。偶尔卸去苦劳重担回家,父亲难免形神沧桑了些,心情冷淡了些,说话生硬了些,但也极难从他斑驳的发梢间嗅出烟草的焦味。
我的母亲成长于山村阡陌之间,寒山古木支撑起她嵯峨质朴的灵魂,碧云湖清纯如酿的寒水浇灌出她澄澈的心灵,流霞一般明艳的山花映照出她窈窕的笑靥。然而,往日窘迫的家境,像肃杀的寒风般叩打着母亲的未来,直至她竭尽所能考上滁县的师范学校,现实的残酷与惆怅仍如影随形。在我翻阅的另外几封信中,父亲宽慰的文字如点点滴滴的细雨,温婉而亲切,徐徐地融化母亲心中的寒冰,消解坎坷与忐忑。
我越细细品读,越感父亲对文辞的熟稔、笔墨的精通,这是我记事起便极难瞥见的风采了。在这些文字里,父亲倾情地阐述自己曾如何寂寞,如何留恋母亲的陪伴,如何贪念那份真情带来的光芒。而现在,父亲与母亲早已成为他们所向往的光源,那是他在楼宇间留下的清澈的灯火,是她在锅灶间燃起的炙热的火苗,随他们从天光乍破,相伴到暮雪白头,温和又热烈,含蓄且深情。
我的十指轻轻抚过这些三十年前的信,仿佛摸到了青春年华的神经末梢,信纸迸发出清脆的声响,仍然跳动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脉搏。彷徨与慰藉、约定与思念,都驰骋于纸上,向着未来延伸。细细密密的笔触,一如轻轻重重的针脚,渐渐编织出生活百态,柴米油盐,真挚而铿锵。愿父母,愿你我,愿天底下心心相印的人们,守着相知的缘分,握紧相守的幸福。
作者单位: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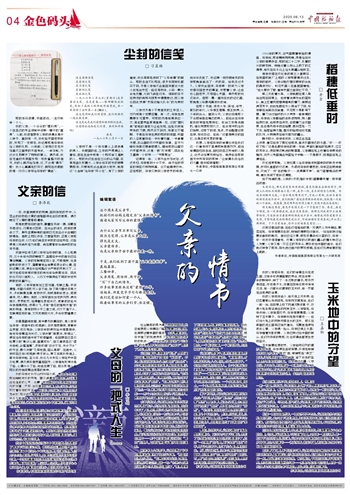

 前一期
前一期